文藝批評 | 金浪:“以情釋儒”——朱光潛的陶淵明論
內容提要:
《陶淵明》作為朱光潛作品中少有的一篇作傢論,極受朱光潛本人的重視。歷來論者往往關註《陶淵明》一文中直接提到的朱光潛與陳寅恪的“儒道之辨”,卻忽略瞭另外兩位沒有直接提及的人物:梁啟超和魯迅。前者作為朱光潛跨越時空的盟友,旁證瞭朱光潛對“情”的解釋並非是從個性與時代之關系入手,而是與其文藝心理學思路有著莫大關聯;後者作為朱光潛刻意回避的對象,其對朱光潛“靜穆”說的批判提供瞭朱光潛後來以儒傢調和思想重新闡述陶淵明的重要起點。二者均證明朱光潛的陶淵明論絕非人格投射說所能解釋,而是其抗戰時期情感論美學構建的產物。
感謝作者金浪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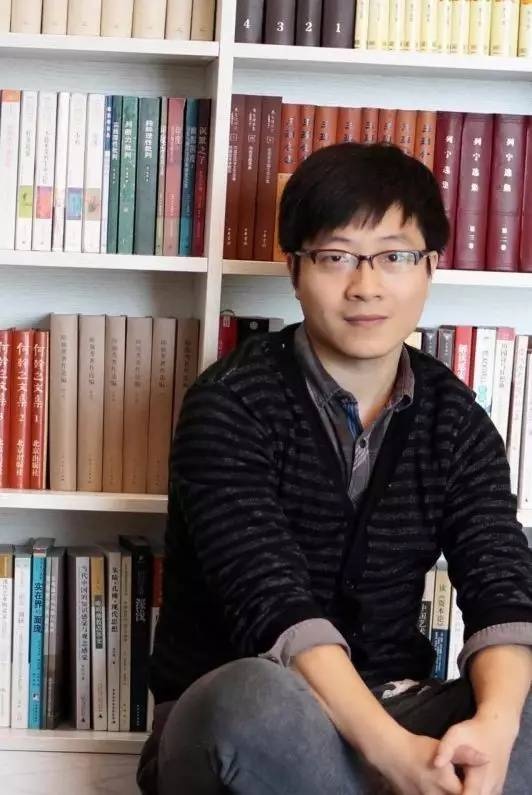
1947年增補版《詩論》出版時增補瞭一篇體例上與全書頗為不同的文章:《陶淵明》。該文最初發表於1946年10月的《大公報》,實際寫作時間可能是抗戰結束前後。按照朱光潛在《詩論》增訂版序中的說法,他本計劃多寫幾篇類似的作傢論,卻苦於沒有時間。[1]盡管在對待《詩論》體例問題上頗為嚴格,但在後來的幾次再版中,朱光潛都保留瞭這篇文章,足見他已把《陶淵明》視作是《詩論》不可或缺的部分。實際上,朱光潛對陶淵明的愛好並非突然興起,而是一以貫之。早在1924年的美學處女作《無言之美》中,陶淵明便是重要分析對象,而其留學期間所寫的《論讀書》後收入《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朱光潛則明確把《陶淵明集》列為自己最歡喜讀的中國書之一。[2]然而,陶淵明之於朱光潛的意義僅僅是出於體例安排上的考慮,又或者純屬個人愛好嗎?在燦若星河的古代詩人中,他為什麼單單選擇瞭陶淵明而不是其他人呢?而《陶淵明》又與朱光潛的美學有何關聯?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還必須從陳寅恪談起。



